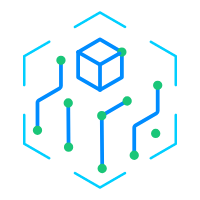文在寅的复仇路韩国最后的英雄十年沉浮书写自己的
文在寅的复仇路韩国最后的英雄十年沉浮书写自己的
的前一天夜里,首尔下了一场大雨。这场雨带来的气温突降,让这座校园的景色一夕之间变了一个样:绕过山脚那座刻着创造文化世界的校训塔,径直前行,便进入一条幽长的林荫路。
就在不久前,人们还能看见这条路上郁郁葱葱的古树,石桥之下流淌的溪水,以及抱着书籍谈天说笑的青年。然而大雨降落之后,虽是秋高气爽、适合贪玩的天气,大学生们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对于这一群青年人来说,这个秋天和以往的秋季有着很大不同。为了反抗军阀独裁统治与十月维新政变,他们纷纷涌入市中心的街道,或是彻夜在酒馆中讨论时事,或是已经被抓进警局。
空无一人的校园里,延绵的枫树和银杏连片地变了颜色,似金、似红,像一场突发的大火,蔓延向上,直至包围山顶的平和殿堂,直到整点的钟声敲响。
19年,一名面容清秀的青年从西大门监狱刑满释放。他的罪名是在维新期间两次带领学生,罪行是站在台上公然朗反韩政策的宣言,量罪是两年。
事实上,韩朴正熙上台的19年正是这名青年考入庆熙大学法学系的一年,坐局子的经历害他丢掉了学籍。他还很年轻,对于前途难免有些不安,但又拿自己没辙,谁让自己偏要跟军斗硬,宁肯不书,也愿为正义和民主热血一战呢?这个热血青年便是文在寅。
19年,22岁的他为入伍剃了短平头,方形脸,有一点青色胡茬,五官十分清峻,只是双唇总是习惯性地紧抿。
有段时间,他喜戴黑色粗边的大框眼镜,不注意的话,你会以为这是个古板又腼腆的书呆子,但当他抬头望向你,你会发现,那双眼睛是那样的大,那样的明亮,好似西方神话中年轻神灵的眼睛,好似里面正住着一颗执拗而生动的英雄之心。
朴正熙倒台后的四十年中,这个国家经历数代,却仍在腐败与新生的轮回中挣扎不休。四年前的深秋,光化门前,头发花白的文在寅高举着烛火出现在反对朴槿惠的人群中,一如很多年前。
东义大学的巨轮再次将从前那名青年推向成王败寇的时代巅峰,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地大,那么地亮,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便是多了复仇的烛火-k22他已做好一切准备,只待破釜沉舟。
新一代的年轻人簇拥着他,而他总愿意向他们露出笑容:他的思绪像秋天的晚风一般飞回去,飞回去,回到人权理想开始的时候,回到与卢前辈相识的那座旧楼,回到成人之初那个惊心动魄,但又美不胜收的庆熙之秋。
当我们试雕章琢句地通过时势造英雄或英雄造时势解文在寅时,年幼的文在寅却站在半个世纪前奔腾的东川江岸,面向我们露出稚子无邪的笑容。
事实上,这个男人的英雄蓝本只是始于一份平铺直叙的情结,这情结源自他真实生活乃至生根的底层世界,也来自他厌恶强权、对抗不公的赤子天线. 弹丸之虑,小国之忌
作为典型的右翼社会,在建国后短短几十年间,以李承晚、朴正熙、辛格浩等精英阶层为代表的亲日派和亲美派将财阀势力捧上国家政治的核心。
19年,文在寅就小学一年级。数年前的战局导致大批北方居民仓促南迁,成为南方地区的贫民,这里面也包括文在寅的家庭。
成年后,文在寅始终记得南方乡下金黄的谷地和广阔的河滩-k22那是他及同学们为了逃避老师催学费,而度过许多快乐时光的逃课天堂。
在这期间,对文在寅来说,学校的知识似乎过于简单,他总是轻而易举地拔得头筹,因此将目光转向更为丰富的领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即便是在乡下小学中,也自然而然形成对金钱阶级的分割,而
学费不成太大问题的文在寅旁观着这一切,他年纪尚小,但已有了鲜明的价值立场,看到其他孩子被奚落,他非但不感到优越,反而产生自己也被侮辱的感觉,因而越发抵触老师的权威。同学们因懂事而不肯回家找父母要钱,文在寅便索性跟着他们一同逃课去了。
19年至19年间服役于特战部队空降旅。这是带有惩罚性质的、亡率的役种,但他出人意料地完成得很好。
退伍后,文在寅重拾学霸光环,通过司法考试,希望捡回被搁置的前途。然而,矛盾却再次发生了-k22即使军阀统治的时代早已结束,首尔之春分明到来,面试的法官仍以他曾领导为由,拒绝了他成为法官的申请。
19年,文在寅在面试中见识了法庭高层的迂腐和可笑,越发觉得这混沌的国土竟与数年之前别无两样,最国防科技大学校歌开出的条件优厚的专属职位,选择回到故土,做一名真正拯救底层民众的师。这一选择带来的蝴蝶效应是巨大的,只是当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
在聊到文在寅时,我们之所以无法不谈及卢武铉,是因为他们之间的缘分是如此妙不可言:泛泛的理想在遇见领路人后,忽然有了真切的光芒。与更为成熟的师卢武铉相遇后,
不过,仅仅高中毕业的卢武铉有着颇为灵活的头脑和超前的思想,借由税务咨询服务,他很快成为釜山当地颇受信任的,与此同时,他还开办事务所,号召们不应独自工作,而应相互协作,各自负责不同的专业版块,实现更精细的领域分工。
19年,法官落选的文在寅受前辈举荐,去往卢武铉的办公场所。在交谈中,两杯清茶凉了又续,续了又凉,他们热切相通,彼此打动,像是阔别多年的故友。在接下来的6年中,卢那座古朴得有些陈旧的建筑,成为了他们并肩作战的场所。
,只能治标而不治本,因此和卢武铉联合在野的人士成立釜山民主市民协会,正式深入在野运动之中。
为了应对独裁政权的背后调查与栽赃陷害,二人一方面立下做干干净净的的誓言
另一方面,则立志要坚守司法程序,遵循刑法原则-k22这两项原则背后的立场和初心是如此的坚定,乃至被一直沿用至他们二人分别成为总统之后。
对于人权事件,两位几乎来者不拒。在为被告人辩护时,他们并肩站于法庭,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卢武铉在警方的烟雾弹之下始终不肯放下高举的拳头,直至被逮捕。这一事件使他名声大振,很快赢得来自全国各地人士的信赖和拥护,人权案件堆案盈几而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站在卢武铉身边的文在寅感到既幸福,又不幸福。他幸福的是在时代的洪流中,在卢的引领下,他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实现,而不幸福的,却是因为通过卷帙浩繁的案件,他再次看见不同的劳动者在社会中承受的苦难-k22这个国家还远远没有好起来。
卢武铉的声望在民间传开。在那个劳动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他自身亦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从到政治家的过渡。
基于个性与早年坐牢的经历,文在寅对于人权理想颇有些轻拿轻放的姿态,他很满足身份,喜欢忙碌但充实的平凡生活。
在这一点上,带他入门的卢武铉却大有不同。多年的民间活动使卢武铉的心在解救国民的愿望中深深扎根,针对自己认定正确的事,他一定要坚持到底。对于这样一个追求纯净和的人,平和的工作方式反倒不适合了。
19年,卢武铉因大宇造船事件遭到检察院拘留,文在寅多方奔走,召集多达名出庭,才得以将卢武铉救出。
事件之后,敌的检方仍向卢发出暂停执业的命令,这直接成了他跨界转行的导火索。他开始思考是否能够运用政治手段,来民间抗争遇到的挫折。就在同年,经过釜山当地协会的商议和讨论,卢武铉受到包括文在寅等律师在内的支持,正式接受的邀请,踏入政治的深渊。
在刚开始工作的几年中,文在寅常常回想起被开除学籍并锒铛入狱当天,母亲追着他的囚车跑了许久。
若干年后,当他在一去不返的人权之路上回首,才恍然发现,原来自己早已一次次地回答过了:
19年,6名中国人因不堪霸凌,在佩斯卡马号上害7名韩国人,文在寅顶着国民的声讨,接受了这6个外国人的诉讼申请,甚至为他们减刑成功。
年过四十的他在针对这一案件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问,他面带笑容地说:
与此同时,卢武铉在政坛中的发展势头也很好。和任何忙于积攒资金、拉拢票数的候选人都不同的是,卢武铉始终召集团队成员,将大部分竞选日程都用于时政与治理的学习。这一踏实、上进且讲原则的风格证明了他是想要干实事的总统,使他迅速获得民众的认可。
他们一人在市井,一人在朝堂,相互分离,却又始终站在一起,不断做出新的突破和努力。距离二人共同的理想,也似乎越来越近。
19年,卢武铉首次竞选国会议员,他的竞选海报虽是黑白的,但透露出来的生机却是盎然的,只因那上面铿锵有力地写着一句:
文在寅钟爱这一版海报,并将海报上的选举口号解为福利国家梦。2002年,随着卢武铉正式踏入总统竞选阶段,文在寅辞别律所,加入筹备竞选的团队,向他的至交伸出忠诚的援手。经过多方努力,二人呼喊着
或许,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是因为当普通人还在以个人幸福为毕生理想时,英雄的眼中早已没有贫富,没有国界,更没有你我。他们的胸腔里升腾着常人不敢触碰的愿望-k22有人称那是圣母病,有人称那是理想主义,还有人称那是背信弃义、牺牲家庭。
东义大学之下,殊途同归,他们二人之所以如此契合,终究不过是因为他们共同享有着,对于更为广阔意义上的人的柔情。
极其疲惫的时候,他望向总统办公室中卢武铉专注的身:怀揣纯真理想的卢前辈啊,即便是从政,也带着那股真挚和执拗的劲儿。前辈的个性从始至终都展现着高度的一致性,再苦再累,他仍在坚定不移地相信,不遗余力地执行。
卢武铉推动国家变化的心情是急迫的,然而,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要让新的治理文化扎根,至少需要十至二十年。
2004年,当选之夜的欢呼仿佛还在耳边萦绕,弹劾总统的呼声却在一夜之间闹起来了,定睛一看,曾经的欢呼和如今的,竟然都来自同一批民众。原来,国家制度漏洞的深处,已传来青瓦台魔咒倒计时的声音。
值得唏嘘的是,我们之所以如此渴求艺术作品,是因为只有在艺术中,那些无限地超越普通人,但又无法等同于神的角色,才能跨越尔虞我诈,跨越生离别,落得一个幸福美满的好下场。
然而这一切并不会发生在理想主义者卢武铉的身上,政治的反噬终究在2009年初夏,将他拽向人生的终点。
文在寅之前的十一任总统因代表着不同集团的利益,他们以5年为周期轮番上台,上演着互相清算甚至构陷的闹剧,除了金泳三,总统们有的没了命,有的坐了牢,最终都是不得善终-k22这便是坊间流传的青瓦台魔咒。
一方面,卢武铉一根筋的个性使他在推行任何政策时都体现出奋不顾身的态度。这一特征曾帮助他获得民众的支持,但在成为总统之后,却
随着任期将至,麾下众人纷纷开始寻求新的依靠,导致卢武铉在交接末期力不从心,给了新上台的李明博事后倒打一耙的空隙。
我心中始终存有悔恨,那就是一开始没有劝阻卢律师踏入政界。在自传中,文在寅这样说道。
文在寅和卢武铉告别青瓦台,踏上归乡的火车。这一年曾是充满惬意与幸福的一年。
文在寅在梁山乡下的新家中养了三只狗,两只猫,还有八只鸡,而卢武铉则在相距不远的峰下村过着农夫的生活,同时潜心研究进步民主主义的著作。文在寅偶尔前去拜访他的前辈,他们仍会向前来拜访的普通劳动者提供最真挚的建议和帮助。
理所当然的,前总统不降反升的社会人气终究被新解为暗度陈仓的政治异变,生之祸已摆在面前。
他还不知道李明博将在他的葬礼上表演一出兔狐悲的闹剧,他也不再管了。他身前那些轰轰烈烈的故事和他坚守了数十年璞玉浑金的向往,一样也没有得到交代,它们全在那个早晨,在一声悲怆的巨响之后,于稀薄的山间青雾中消散殆尽了。
如果说英雄的诞生类同于太上老君七七四十九天炼丹的过程,那么,卢武铉的身故,就如最后那味痛彻心扉的三昧真火,炼就了复仇总统最后的悲壮。
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温暖、最炽热的人。可以想见,叫一个赤诚的理想家亲眼看见恩师连同挚友破碎的尸体,看见他们多年的心血再次被居心叵测的佞踩在脚下、散作扬灰,经历此番创伤,他心中很坚固的一些东西,终究轰然崩塌了。
中断律师生涯并进入青瓦台的选择曾使文在寅感到浑身不舒服,就像是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坐在了一个不合适的位置。
然而,卢武铉后,他忽然发现,从相遇到别离,从在庆熙大学校训塔下喊口号的那天开始,到涌入拥挤的人潮大声呼喊拒绝弹劾卢总统!为止,四川农业大学地震的课题从未打算使他从这张责任的椅子上解脱。
现在,与其说文在寅上台是为完成卢武铉未尽的课题,不如说是他一直以来按捺在内心深处的血性在永失挚友后再次苏醒。
前辈,你每天需要了解和处理比旁人更多的工作内容,为何你开会时从没困过?卢武铉则回答他,
韩国财阀在短短几十年间,像打造韩流明星一般,将韩国塑造成了亚洲奇迹。然而,在这背后,却是不断扭曲的经济结构性矛盾、与日俱增的社会丑闻、以及世界第三的自率。
在外交上,他拒不支付萨德系统,拒不承认萨德布局,积极缓和中韩关系,同时促成金正恩跨越国界,展开会晤。
他终究体会到卢前辈曾遭遇的矛盾和苦楚,更加懂得了他的坚毅和沉默。在夜深人静、伏案工作的时候,他忽然感到揪心和后悔:如果当初再陪他走过更多路程,如果当初能够再努力一些……
文在寅完成名为《东义大学》的自传。这本书虽名为自传,却起笔于他和卢武铉的相遇,停笔于他们的别离,仿佛27年并肩同行的深情,已构成文在寅的一生。过往27年的深情,更是书写了他自己的十年沉浮。
看看吧,背叛者们,他是一位多么坚毅的前辈;看看吧,财阀们,他是一名多么高尚的圣贤;看看吧,媒体们,他是一个多么干净的体面人;看看吧,国民们,他是一位多么仁爱的明君!看看吧,让世界与我们的后代都看看,你们是如何亲手将他送往心如灰的地狱。